城市更新中的怀旧牌:不是不能用,而是要因地制宜
作者:admin | 分类:房产资讯 | 浏览:64 | 时间:2024-11-18 14:01:27上海新天地地区改造是迄今为止最早、最成功、最知名的城市更新。自取得巨大成功以来,大量商业地产和城市更新逐渐开始热衷于打怀旧牌。但这是怀旧卡吗?万能钥匙?
答案是否定的,尽管这不能否认怀旧牌的舞台性、创新性和引人注目的价值。因此,有必要客观评价和表征怀旧情绪,特别是怀旧情绪与城市更新的匹配程度。
先得出结论:怀旧不是不能用,而是不能反复用,必须因地制宜地使用。
1、修旧如旧,一窝蜂。成功其实是有重点的。
引用开头提到的上海新天地的案例,就是以当地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会址为来源。在高举历史文化典故大旗的同时,周边地区纷纷效仿,乘势而上,开展“修缮旧建筑+填平娱乐产业”,内外混搭成为一大发展思路旧区改造、城市更新乃至商业地产。
然而,今天已经无法对新天地案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奖励:
是大殿的故事线创造了新的世界吗?
还是旧建筑的修复创造了新的世界?
还是酒吧街的大胆创造了新世界?
可以说,人人有贡献,但独木难成林。只能说,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地点、特定的建筑形态和适合的商业业态意外地相遇,从而创造了一段美好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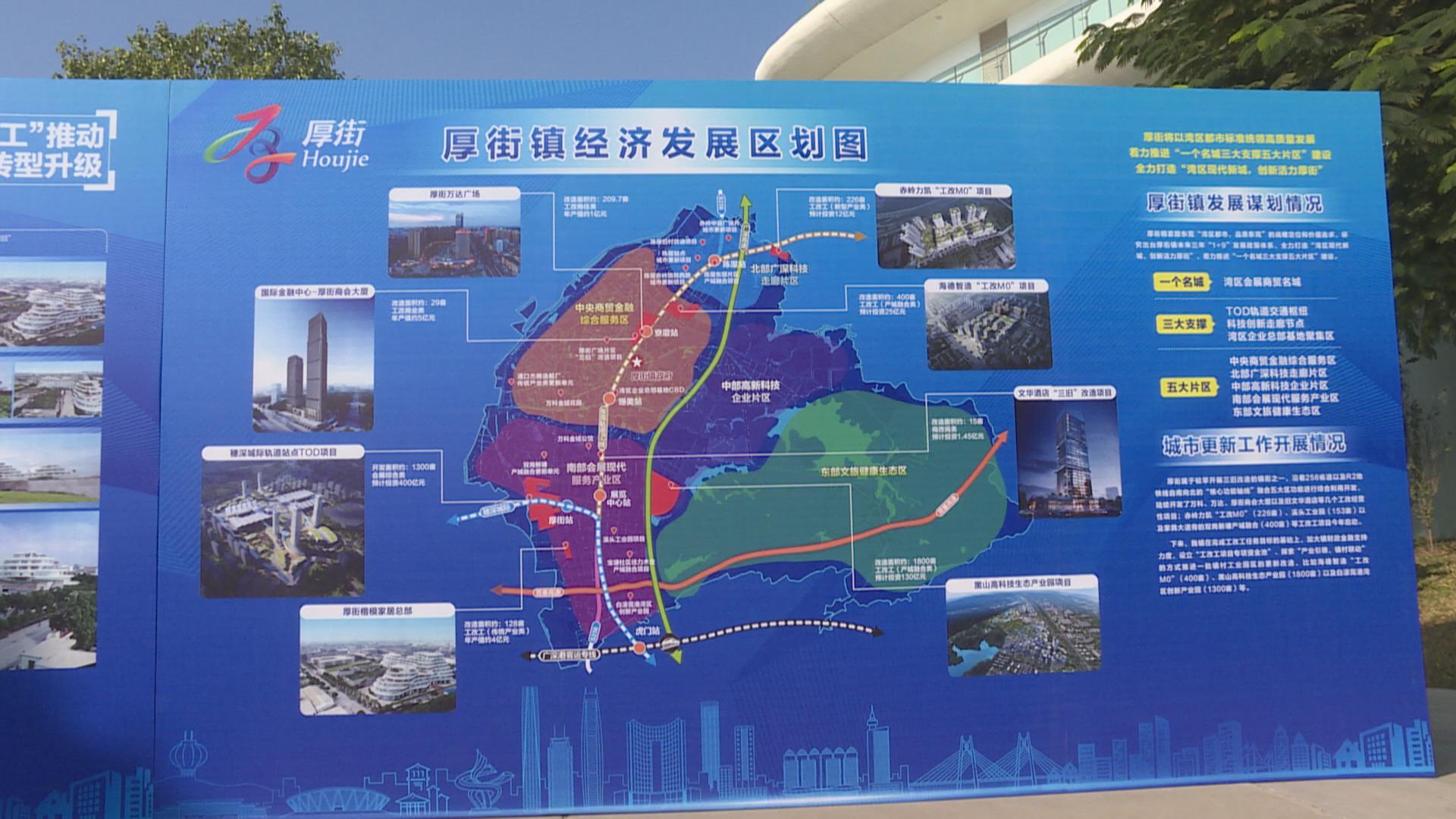
你可以致敬新天地案例,但绝不能依靠时间、地点、原有的建筑条件去建造一个新的世界,因为——如果只是换个地方,建造一个新天地,会“保住大繁荣”吗?
肯定没有哪个交易者敢拍胸脯吧? !
言归正传,单从“填乡愁”的角度来说,每个城市基本上都有物质,但这些源远流长的历史人文、如今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都不同,即使背后还有人,各有各的自己的侧重点,值得盘点和分类。
仅以上海的成功案例为例,桥梁桥梁也可分为三类:
第一个是“上帝会赐予你食物”包括原来的位置和建筑。即使未来有很多升级和改进,如果没有前者原有的优势,未来也是枉然。最著名的有百年的网红外沙滩、城隍庙和如今每天人头攒动的武康大厦;
二是先天优势(位置或者建筑),然后“把内容变成故事”,让它成为不断成为网红的微载体。同时,也反哺了建筑的品质,给内心带来怀旧之情。代表案例是南京路。国际大酒店的蝴蝶饼和淮海路光明村的鲜肉月饼,都是怀旧品牌的简约创新版。
第三个是黄河路。虽然它的历史只能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美食街,虽然它的位置领先于同时期的乍浦路,但电影《繁花似锦》所勾起的情结却让黄河路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说是怀旧之情掀起了黄河路的更新,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或许这就是新天地巨大成功的早期边际效应。怀旧的招摇在过去十年里已经得到了尝试和考验。新天地创富团队后续的一系列手段,从太阳宫到盘龙天地再到红手坊,都失败了。它是用怀旧的逻辑重新复刻的,只不过是把原来的品牌、建筑、业态“各取其一”,用怀旧的方式加持之后,才有了今天不一样的怀旧面貌。

2.怀旧有三张卡,但怀旧没有回购。
哪里有成功的地方,哪里就有不够成功的情况。
首先要说的是:今天讨论的所谓怀旧卡不仅限于建筑作为创意蓝图,还捕捉食物和烹饪,从“先天”的地点、街道、建筑到后天的大大小小的(成就主题传播) IP,从当地的名俗、特色美食、名人目击、电视剧甚至拍摄地,无不高举着过去的情怀,瞄准了今天的商业转型。它们都是城市更新浪潮中怀旧的变革镜头。
近年来,或与上海新天地相媲美的持续传播周期,文和友品牌位于湖南长沙:是一个附属于文化和旅游的线下商业(或城市更新),左有怀旧,有民俗。右手风俗,使其成为具有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长沙本土品牌。一时间品牌无人可比。
然而,类似的运营策略离开了长沙,被嫁接到广州和深圳。虽然也以“红利”的形式引进了一大批长沙特色餐饮品牌,如本锣埠浏阳酒家、都铎辽记跳蛙、茶颜悦色等,一度吸引了大量消费者,但如今的经营状况不理想。民俗已经离开了支撑它们的发源地。即使受到城市特定政策的约束,他们所面对的消费群体也长期接受不同“派系”的文化消费。正宗的仿制永远行不通,甚至根据处方适当本土化的药品也似乎水土不服。
回到上海的案例,今天的新天地在长虹依然是网红,但上述坚守新天地套路的太阳宫、盘龙天地、红手坊,绝对不如新天地的“大本营”有多久的信心。他们可以继续受欢迎。这就引出了上面这篇文章的担忧“让新天地成为可能的最大基因是什么?”
近两三年,上海出现了很多怀旧的陈词滥调。每当一个新项目开业时,至少在某些特定楼层,要么是装修风格、场景营造,要么是业态的引入。它采取了城市名俗的怀旧策略,一度在网红中红极一时。然而,笑的只是新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怀旧的场景也无法阻挡整个项目的颓势,“三五月各领风骚”。就连“怀旧”的专属楼层,也因为导流效应而逐渐失去人气。
怀旧三张牌:老房子、老故事、老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一方面,喜新厌旧是消费群体的天性。上海每年新开的商场、新项目,已经催生了“只拍照、打卡、不花钱”的消费惯性。 “最多一次消费”的习惯在全社会的消费中得到保护。降级棉袍下,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怀旧本身就是一次性产品。如果不抓住有限的网红周期,迅速将蜂群转化为生产力,虽然并不意味着“怀旧不能吃”,但最多也只能吃一次。
所以问题是:谁应该受到责备?
怀旧是一张卡片。年轻人的消费是好奇,老年人的消费是回忆。然而好奇心不会再回来,回忆也不想再回到那些日子。
正如“成功的两个标准,一是流行多久,二是转化生产力”一样,怀旧也有两个标准:一是让老年人一遍又一遍地比较怀旧,二是让年轻人产生怀旧的感觉是值得传承和时尚的东西,但这当然并不容易。
如果不可持续,就不会回购。
3、怀旧成功的背后,一定有“可控发展”
那么,从以往怀旧的成败得失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致客观的结论:
1、成功来自天时、地利、人和。仅有怀旧是不够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2、成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可能是业态、地域、客户群体的空白点;
3、怀旧也有地域特色。一地老,另一地不迎,国家战略需谨慎;
4. 怀旧在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中都不占主导地位,因此怀旧卡本身是一个附加问题。
在对过去的拆解的基础上,为了弘扬过去、开拓未来,未来的城市更新是否应该使用怀旧卡?
答案也分为两种:
一是因地制宜。如果项目地点本身就有一个好故事,那么就不要忽视它。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做生意尤其不可取;
二是控制性发展(怀旧卡),包括管理者对区域城市更新项目的战略选择和交付率,也包括具体案例的运营者。即便要打怀旧牌,也必须思考如何“旧事重提”。 “老到最后”而不是“老到最后”。
有什么想法吗?
怀旧卡在过去成功和失败项目中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它既不能享受专属欢呼,也不需要为项目的失败承担责任。与其讨论“是否怀旧”,不如升级为“如何利用怀旧”作为新命题!
上海还有一个市中心城市更新项目,叫金潮八弄。一开始我以为是抄袭新天地公式:房子有历史、有故事,如果里面摆满了一些快速消费品或者潮流商家,那就是新天地虹口店了(毕竟和以前的不一样)太阳宫,这是一座有着古老故事的新建筑)。
但事实上,金潮8号开业以来的几次调整和优化,到底是基于一切尽在掌握的规划,还是基于市场的变化。总之,如果把新天地解读为“老建筑+新消费”,金潮八巷就是“老房子+新艺术”,再加上各个露天市场的紧凑排列,似乎后天已经习惯到了极致,但或许——与新天地只是一处不同的位置!
位置不仅仅是位置。这背后隐藏着因区位水平差异而造成的人气、旅游资源、漫无目的地消费概率、客均价格、周边消费群体素质等一系列差异。总和相差很大。告别。
在我的印象中,8巷的怀旧牌非常内敛。建筑的历史只有在开幕阶段才会被探索和触及,随后就是不间断的艺术展览。无法揣测交易者对怀旧的态度。他们要么是觉得不想重复新天地的发展道路,要么是看不到怀旧的可持续转型,干脆直奔大地——艺术!
但如何拍出怀旧的电视剧这个话题却一直存在。
一是怀旧出道后迅速与消费对接,就像太阳宫的老上海弄堂场景与大排档的互动,但“成功是怀旧,失败是怀旧”,海派场景决策也有限对于小吃的种类和品质来说,如果时间一长,上海场景和上海小吃不能迎来源源不断的游客,那么相对于南京东路来说,它们就会失去地标性的地位。
另一种是打牌后迅速将怀旧与今天联系起来,比如同一地点、同一场景的旧貌和新貌。毕竟后者在承载业态上更具包容性和多变性。毕竟,年轻人对于老东西只有好奇,没有情感。在老人的怀旧情怀中,“铭记苦大于甜”。吃一次就够给面子了。
所谓受控开发,既是控制又是开发,或者说是以控制为背景的开发,有发展的空间。这既包括当地管理部门的选择策略,也包括管理部门、业主、经营者的选择策略。游戏在他们之间来回进行。
说到这里,我们就来说说房地产:2024年初,上海楼市不断传出黄浦、静安、徐汇等“市中心中的市中心”将推出大量所谓的“城市中心”。称为风情别墅。其中,还有虹口杨浦“紫娇”等传统“非上海”别墅也想分一杯羹,但结果如何呢?
凤灵山庄产品的优缺点暂且不说。只能说,盲目推出、盲目上市的结果就是,今天要么有价无市,要么无市。如果我们懂得控制发展,甚至懂得“惜售”,我们不就是今天的样子吗?一起吃个饭,吃个痛快不是更好吗? !
从房地产到商业再到城市更新,粥多了却只有这些是和尚。没有计划,没有策略,没有顺序,也没有选择。怀旧是一种策略,至少你不应该承担责任。
